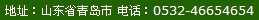|
卤米松乳膏白癜风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al/140813/4447737.html当年明月 石宋华 一庚子大疫,沉沦空巷,缩头弓身,作鸵鸟状,只求苟活一时。虽说贱命一条,但也不想时代的那粒灰落在自己头上,熬过去总比趴下强。年关将近,学校下发通知,用“米”字着重提醒,说是来年中考将有重大变革,需到蕲州走一遭,参加会议,探听虚实。驱车前往吧,这可是养家糊口的营生。动身时,天色变得扑朔迷离,临时添了件内衣,还是觉得天不地道,人难舒坦。车过武穴,风声骤紧,乱云在头顶垂成泼墨。这样天气,多半会降温降雪。等到雪子拍窗而来时,哔剥之声,铿锵有韵,反倒有点易水送人的意味。同行两位美女皆健谈,一路神侃,倒免去不少旅程困乏。过福银,上麻黄,一路飚行,苍苍茫茫,好不自在。新奇的是道上竟空无一人,反倒让人心里空落落的,怀疑走错了路。要知道我们一行三人,都是路盲。靠着车载导航一路前行,一旦跑错,孤男寡女,后果可就严重了。路上引发联想:“这导航怕是收了麻黄的好处,不然怎么把我们导上这条鸟不拉屎的高速。”“说的是,这也叫高速,一个鬼影子都见不着。”好在是路终有尽头,天色将暗时候,总算到了蕲州地界,骂骂咧咧走下道时,却忘了还要回来。如此不厚道,怕遭报应。返程时,果真应验,莫名又出错,麻黄在谈笑间被完美错过。跑了一晚低速,累个半死。倒应上一句谶语:你现时爱理不理,到时可高攀不起。冥冥中,这麻黄怕是通着灵气,脾气大着呢!到了地头,雨意阑珊,不想碰上多年不曾得见的师范同届同学蔡林秋。在宾馆大厅,秋兄远远立着,挺拔高标,只是鬓角已有霜花泛起。凤栖一别,当年倜傥少年,如今已是半老徐郎。晚上,拥衾闲聊,自然地扯起凤栖山旧人旧事。影影绰绰,一来二去说了个七七八八。秋兄妙人,谈事纵横捭阖,说人风云际会,波诡云谲陈年旧事经他一说,竟显出盎然生趣。末了谈起“情系凤栖山”征稿事宜,秋兄居然向我约起稿来。我一惊,想不到如我一样穷教师一枚的秋兄,整日穷忙,居然还干上了情系凤栖这类苦逼差事,斯人情深,倒叫人好生慨叹。虽搁笔多年,无奈盛情难却,熬了几宿,写了几页小字,终不成章,权且当成有关凤栖的残篇,了却一桩心愿。二上凤栖时,正好十四五岁,说是响应召唤,不如说是解决吃喝温饱。那年月,读师范,是铁饭碗,国家包分配。父母年龄大了,承受不了漫无边际的未知,有吃有喝的现实倒逼着他们定下孩子上师范的决心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父母之命大过天,不从的话,那可是皮痒痒,得用家法治!单打不过瘾的话,双打可就要粉墨登场了。刚来那阵,娱乐活动层出不穷,一群傻小子刚从紧张的书山题海中挣脱出来,自然乐得逍遥。课程也简单,几本代数几何,外加文选语基,睡在床上也能混个及格,一时间,谈天说地倒成了热门科目。只是离家日久,想家倒成了解不开的心结。好在节假日接踵而至。那年中秋国庆串在一起,一连放假八天。学校考虑周全,包个大卡,只是客运的车辆紧张,临时安排的车次定在了早六点。马上要回家了,一群傻小子竟闹腾了一宿。早晨天不亮就有人嚷嚷上了,倒水的,洗漱的,起床的,赖窝的,一时间乱成一团。我从走廊经过时,只听得尽头有人惊呼:“呀呀呀,好大的月饼!”难不成,有人发月饼。此等美事岂能错失。争着向前赶时,先到的人却停止了喧哗。黑乎乎的一大丛人伫立着,伸颈仰望。顺着方向望去,嗬,好大一块月饼挂在西山树梢上。通体透明,色如鹅黄,就那么硕大无朋的挂在树梢,压得树梢婀娜弯腰,曲背生韵。在它普照下,校舍操场礼堂都蒙上一层清辉。其间,游弋的雾气丝绸般滑过,淡定得不可方物。这倒使得我们平时活动场所显出一种神秘气息。许是起的人多了,惊起栖在树上的鸟雀,枝丫上鸣声响起,响过之后便是振翅盘飞。背景是圆月,剪影是鸟雀,黑黄相间,一瞬而过。像画图定格在眼眸,这么些年,从未忘却。从山上下来,坐车里忍不住回望一眼,那轮浑黄的圆月依旧静穆地注视着,不曾倦怠。多年以后,教《故乡》,读到少年闰土一章,就会想到它。依稀往梦,像是一个守望,一别经年,更成一份挥之不去的挂念。快毕业时,和几位外乡小子绕凤栖山逛了一圈。凤栖北高南低,北坡舒缓,南坡陡峭。学校正处南坡,依势附形,修路建校,应是颇费周折。倒是北坡几户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安逸得很。北坡植被茂密,林中山味飘香。有一家种了枇杷,挂果时节,鲜黄嫩绿,着实诱人,忍不住偷摘下来,快扔入口,马上吐了出来。酸呵!到现在我都不喜欢枇杷,那种酸涩怎能叫水果,充其量是味药材。为什么那么一座屁大的小山称凤栖,真不知何因。有一年,看了一纸闲书,书里说“旧说南阳有菊水,水甘而芳,居民三十余家,饮其水皆寿,或至百二三十岁”,这是苏轼考证桃源的去向以正视听时留下的笔墨,可惜信者寥寥。以此类推,当年怕是有位骚人落居此处,想着有凤来仪,以致以讹传讹,像真的有凤凰在此落脚一般。时过境迁,如今当有人问起,我想我也一定会说那山上真有凤凰呆过,千真万确。三在凤栖呆了三年,正经的学业场景忘了,有两起闲事倒还记得。事关两个地名,一曰兰溪,一曰绿杨,挺有文艺范的。其实浠水这个地方文艺范的地名挺多,不像黄梅,天门村,五祖镇,古塔西路,一听就觉得到了佛天圣地,不得妄为。哪像兰溪、清泉这样的称谓,十足烟花迷津气象。不提也罢。进兰溪,是有位叫袁绪秋的仁兄,此仁兄虬髯黄须,为人大气,相处容易。有一年春夏之交,放了假,一行人结伴去他老家兰溪。上车下船,巅簸好几个时辰,总算一睹印象里的水乡风光。远处沟渠纵横,码头人声鼎沸,人挤人,总算没掉到水里。印象最深的是水里的鸟并不怕人,细眼小脑呆在船头不远的水面上,自在晃悠。时而入水,时而呆立,大声驱赶也不飞走。同行一位捡个石子扔过去,石子入水击起水花,小鸟只是转了下小脑袋,乜斜着瞟上一眼然后继续紧盯水面。好执着的小鸟,不知叫什么。如今再碰上,定要抓上几只,拔毛去脏,撒上几撮胡椒,一定好吃的紧。可惜可惜。袁兄家在水乡一个大坝上,周围是满荡茂密的水草。晚上吃饭时,迎接我们的是满桌子的水乡菜肴。鱼是清蒸的,嘴小肚大,皮肉紧实。大汤锅冒着热气,汤色乳白,皮肉鲜嫩,怀疑是传说中的东坡肘子。还有芡实的根管,俗称鸡芭管子,太野,却是因形附名,不好斟酌,一旦推敲定然哭笑不得。最地道的是风味豆豉,上盖青葱,下藏红椒,滑齿而过,有一股陈年酱香刺激味蕾,真可谓风情万种。袁兄父母笑盈盈看着,举箸下勺,很少言语,倒是袁兄在大声地招呼我们这群瘦骨铮铮的饿汉。那年月,物资紧缺,那顿水乡丰盛的家宴,带着它独有的烟火迷彩,氤氲了我关于生活的最初梦想。吃得饱不行,还要像今晚这样吃得好才行。晚上躺在床上,八卦男女,风情人事。想不到这群就要为人师表的家伙一肚子儿女情长。单拣一个皮肤,就能分出嫩的鲜的,软和的和硬实的。白是统一标准,黑也行,但要黑得别出心裁方能别有洞天。如此大的学问,真要通识个中三味的话也真够费神。只是“硬实”一词太费解。有位仁兄说了开来:“那可要等到尝过才知晓。软和是用来摸的,硬实只能是吃,烂了不行。嫩鲜是用来看的,中看不中用。”当时脑子里灵光一闪,这家伙不就是传说中的流氓大亨吗?天马行空地听他神侃,心旌飘摇地质疑反馈,反倒勾起了有关女孩子的许多幻想。只是太复杂,想着想着,脑仁生疼,衣袂飘飘,跟着周公厮混去了。半夜时,一阵鼓鸣把人吵醒,一睁眼,一群人还在挺尸呢!循声望向窗外,咕咕——呱的叫声惊天动地,似是来自窗外苇荡。趴在窗台上,凝神聚目,可惜月意朦胧,昏黄的轮廓始终看不分明。河风漫拂,特有的水草香味似有若无的从鼻间拂过,这时才明了这鼓声是漫天的蛙鸣。细细琢磨,这蛙鸣自远方发起,在水荡深处汇聚,依次到坝脚处共鸣,连带的,房檐下的蛙鸣也响成一片。这声音排山倒海,如金戈铁马般叫人错愕不已。我怀疑江南水乡就是这般光景,人事风流,物事繁华。难怪柳永慨叹江南有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“菱歌泛夜,嬉嬉钓叟莲娃”。有一年去三峡白帝城,看了一眼白帝托孤雕像:刘备语沉,孔明眼深,扶榻的阿斗惊恐莫名。那时就想,这阿斗也着实可悯,做一江南富翁岂不甚好,清风朗月,强似勉为一国之主,到头来却落了个扶不起的恶名。如果阿斗生于袁兄这等人家,只怕豪爽之气随生,风云之骨渐长。水乡一别,实堪回想。到绿杨,其实是个意外,那段时间家里出了点意外,应当寄来的补贴没有了,一连几日吃着萝卜盐菜,舌头都吃出水泡。同寝室的室友也都难兄难弟吐着苦水,高忠平站了出来,力邀室友去一趟他家,聚聚聊聊。一番盛情,欣然起行。到绿杨时,哪有一株绿杨,风尘仆仆的路边倒是见着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人。他是高爷,见了我们,手忙脚乱招呼着。下车,上道。乡村土路高低不平,我们到的时候,天已大黑,有人走着走着崴了脚。高爷在前面带路时小心提醒转弯,过巷。在一处老旧的青砖瓦房前一行人总算落定行程,剩下的就是吃了。刘恒说,狗日的粮食,既嗔还痴,何苦呢?吃,不分贵贱,难辨贤愚,对我这样的吃货就是永恒的主题。桌上摆了酒,房里却没了电,点着油灯,影影绰绰,一行饿急了的家伙第一次感到吃的庄严和急迫。酒是自家酿的,挺辣,天冷,又是第一次喝,却不觉得。一杯下肚,顿觉四体生火。好温暖的一股热流从脚底升起,一行人也不用劝,噼里啪啦地就自顾自喝上了。连喝几口,感觉有点异样,这头嘛竟重得如同水牛。站起来夹菜,朦朦胧胧想夹块白花花的肉,结果到嘴的是块明晃晃的土豆,等到再去夹时,那块肉早不见踪影。摇晃着上床时,意识到人已大醉。半夜时,喉咙里像火一样烧,急着找水喝,高爷披衣提灯早把水倒在事先凉好的温水里。原来高爷知道这酒劲大,本不想我们多喝,又不好制止,只好事先凉好水,等我们找水喝。那次头痛了好几天,奇怪的是后来却把酒当成了生活经典。时不时温二两。酒中人意悬浮,杯中快意恩仇,也就因此惹出许多麻烦。听说高兄如今抱得美人归,常做逍遥游,酒乡一别,寄意山林,倒不失人生一大快事。四凤栖山尾有一方流水,绕城而过。枯水季,细沙如银,涨水时,浊浪滔天。临毕业那年,教文选的是一位姓南的先生,大小伙,人挺精神,名字忘了。有人向他提议,晚上去河滩搞个篝火晚会,他竟一口答应。傍晚时,都很兴奋,早早吃过晚饭,路上边走边捡能烧的枯枝败叶,天快黑的时候,肩挑背扛的还真到了河滩上。五六月的时侯,河里无水,河边少风,选个开阔点的地方就把火烧了起来。熙熙攘攘的人流绕着火堆跳起了刚学的交谊舞,伸胳膊动腿的,好不快活。只是少了点音乐。这时候,就有人跳出来欢唱了。男的叫刘政,女的叫姚红妮。歌名《敖包相会》。那晚,月挂中天,周遭如水空明,唱的欢实了,还真应景。当唱到“只要哥哥你耐心的等待哟,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走过来”的时候,就有人开始起哄。哥哥妹妹的叫得特别欢畅:有只唱妹妹的,有只叫心上人的,有记不上词瞎哼哼的。到底谁爱了谁,谁又负了谁,如今已无从知晓。只是那夜的篝火忽明忽暗,当时并不觉璀璨,而今却活色生香。有一年听李健唱《贝加尔湖畔》,极力渲染两个人的篝火,好生凄美,如果当年,也有那么一位女子,我心醉汝,只怕最终也是落得个水尽鹅飞罢!庄生晓梦,暖玉生烟,想想就好,千万当不得真。前些年看了篇《一代中师生的芳华》,满屏的辛酸,透骨的伤寒,引逗起海潮般的共鸣。而其实那一代人的芳华,又何止中师呢?经历是最大的财富,有经历,方生感慨,感之一生,念必将至,心心念念倒不失人生真意。明月依旧当年,尘世几番游走,伤情也好,快意也罢,又何须执念那一抹历史回眸间的苍凉!作者石宋华现任教于黄梅县第七小学张桂梅 |
时间:2021/12/11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郑氏的起源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